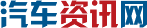解读父亲
2020-03-10 03:13:45 菏泽汽车网
父亲是一部无字禅书。
需要一生去参悟解读。
真正读懂了,也许他已经走了。
父亲鬓角的白发,额头的皱纹。
写满了担当和父爱。
只看他的背影是远远不够的…
题记
1929.12.04—2016.10.28。
数字中间那一短截横线,是我父亲的生命区间。一个人生平的一切,竟可以省略成一个符号,人呀,还有啥想不通的?
父亲出生,世上还没有我;父亲过世,我守在他身边。他咽气前数小时,我还和他说着话来的。时针走过子时,弟弟火急火燎地在电话那头说:老爷子快不行了!
十来分钟后,等我赶到病床前,我连叫了几声‘‘爸爸’’没反应。我知道,父亲真的走了,永远地走了!
我平静地让弟弟回家做一些该做的事情,便紧挨父亲坐着。病房里就我们爷儿俩,三维空间和空间内的物件入目皆白,而窗外则是一片漆黑,白色、黑色,都是瘆人的颜色—透着冰凉之意;时间不管不顾地循着规律而走,走得悄无声息。往日,爷儿俩相对无言有过,可那是俩回事,从未像此刻这般寂静,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音。我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过父亲的身体,期望能发现那个渐渐僵硬的躯体,意外有一丝细微的生命迹象存在…
没有奇迹,我失望了。于是,无边无际地想着代表他生命过程的那段横线,以及横线所蕴含的所有情感文化元素…
早年深秋的一个早晨,五更的鸡鸣声把一个不到6岁的小男孩吵醒了。
或许不叫醒的,而是他太兴奋了,是自己巴望天早点亮,醒了。因为,今天要带他出远门做客。至于母亲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借钱,当然不会告诉他。
第一次出远门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,很正常。何况要去做客的亲戚是个有钱人家,那亲戚他叫姑姑。小男孩起床后就翻箱倒柜找像样的衣衫,翻来找去只见一件冬天罩棉袄的衣服没补丁,于是便穿上身催母亲的早饭…
娘儿俩走了二十多里山路,走到晌午时分才到。男孩姑姑见娘家人来了,还带了鸡蛋和她爱吃的粉干,便热情招呼吃饭。
上桌后,男孩见桌上有鱼有肉,眼睛贼溜溜地围着一两盘菜转动,但就是不动筷子—出门时母亲交待过做客要斯文。男孩姑姑便怜爱地帮他夹菜。
姑嫂俩边吃边聊,渐渐往正题上靠。男孩母亲说:娘听说你又怀上了,就让我来看你…
没等男孩母亲的话说完,男孩姑姑便叉开了话语:哎呀,你看,要不是你姐夫前一阵子做生意蚀了本,手头有点紧,我早就回家看娘了。
男孩姑姑心里明镜似的,老家来人多半是借钱,这个弟嫂是娘5个儿媳中最喜欢的一个,现在把娘抬出来,用意很明显。
男孩母亲是要面子的,听这话音,已知晓借钱无望,便不再说下去。桌上的气氛骤然沉闷下来。吃完午饭,提出告辞。男孩姑姑客气地一边挽留,一边塞给男孩5元钱纸币。临别时,还叫男孩抓些炒豆子路上吃,男孩不论大人怎么催促,依然怯怯地就是不动手。后来,他姑姑抓了几把放在他口袋里。
路上,男孩母亲问他为什么姑姑叫他抓豆子不自己动手,他回答说:‘‘我自己抓,不好意思多抓,姑姑真想给我,她会抓。她抓,不好意思少给。’’
这件事,回来说给男孩父亲听,他父亲挺高兴,没借到钱的不快一扫而空。愈发喜欢上了这个孩子。
男孩这次做客的收获,不是吃到鱼肉、豆子,而是通过比较,得出一个结论:种田家里穷,做生意家里富。不想种田的念头,就深深地种在他心底。
男孩长到十六、七岁时,就时不时地往外跑做生意,跑一次,家里派人抓回一次。他父亲不是不让他做生意,也不是担心他不会做生意,而是考虑外面兵荒马乱,怕出意外。
20岁那年,男孩又寻机逃离家乡。他叫小他10岁的妹妹隔三差五地偷拿他的衣服,今天一件上衣,明天一条裤子,拿得差不多了就跑了。
他在家乡附近的火车站做挑夫,帮着溃退的军政人员家属搬运货物,收入倒也不少。可好景不长,不到三个月又让他父亲逮回家了。
家里为了拴住他的心,寻思给他娶媳妇。可说了几头亲,不是他看不上别人,就是别人看不上他。后来,终于有一户人家的女儿让他看上了,人家也答应他上门相亲。他穿戴整齐,在媒人的引领下,提着礼盒登门。准岳父凭胆识靠力气种出了百十担田地的家业,见面时一看这后生貌不惊人,个子矮小,心甚不悦,不让女儿出来相见。本想立马打发走人的,碍于媒人情面,姑且留人喝茶再辞。
未曾想,这一留,有了转机。这男孩反客为主,又是倒茶又是递水,殷勤备至,说话伶牙俐齿。准岳父渐渐有了好感,于是就试他力气。但吐出口的话却是:‘‘你们坐一会,我去挑一担谷子回来。’’男孩反应很快,马上接话:‘‘我去,我去!’’
他和他的准郎舅挑着大箩筐便出了门。路上,他暗自思想:凭自己力气挑不起一担湿谷,得想办法做些手脚。他首先与准郎舅搭腔套近乎,拉近彼此距离。走到田里,男孩将准郎舅支到另处,悄悄地在箩筐底下塞些稻衣,满满的一担谷就轻快地挑回来了。准岳父见其人小力气不小,有些诧异,就又让他挑甘蔗。男孩故伎重演,又在其间夹杂蔗衣,顺利通过了考验,从而‘‘骗取’’了一段姻缘…
这个男孩便是我父亲,这故事是奶奶讲给我听的。
父亲婚后,还是跑出去了,但不是做生意而是做工。母亲曾与我们谈起早年的父亲,说他人是机灵,可有时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
‘‘那年在煤矿,你们姐弟都出生了,粮食定量不够吃,有钱也买不到吃的,他就偷改粮食本子,把余额数字改大,蒙混过去二、三个月。后来被人发现,把本子都扣了,受到单位的警告处分。这件事,影响很大,粮食供应部门正想抓典型,要不是他工作表现好,领导出面说话,说不定会被开除了。后来也是因为这桩事,导致全家以‘亦工亦农’为由下放回了老家。
你父亲回乡种地,农事生分,工分不高,养家糊口靠下放金度日,还整天指责大队、小队的头头脑脑这不对那不对,得罪了不少人。一年后钢铁厂招工,你父亲认为这是个机会,坚信‘出路出路,出去就有路’的说法,可大队的人不放,他就找公社领导理论。结果,人家把他当‘瘟神’送走了。’’
熟悉父亲的人,都能讲出一些故事。我先约略地概括一下,在人们的眼中,父亲的形象是这样的:
有人说,他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…
有人说,他是一个受人敬重的人…
有人说,他是一个眼不揉沙的人…
父亲自己并不看重自己,至少没觉着有多少成就感,有时还会流露出‘‘生不逢时’’的感慨。
评价一个人,与评价一段历史一样,永远不能完全揭示真实,只能有限接近真实。别人不可能全面反映客观,自己又何尝真正认识自己?所以,对待别人的评议,听到赞美声,别昏昏然;听到贬损语,也别心里去。
誉欤?谤欤?活着时,做真实的自己,随人怎么说;死了,无所谓,当然也管不了。这是父亲的一贯观点。现在父亲走了,没有痛苦地悄然辞世。走的很突然,未留下一句,便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。
父亲这一走,让我明白:其实,人不论活多久,都是活在此刻。此刻之前已逝,此刻之后难料。同时,让我醒悟:我在尘世上做儿子便到了头。因此,‘‘母亲节’’‘‘父亲节’’于我,只是一种伤痛的思念…
籍籍无闻的父亲叫刘光献,尽管现时为信息年代,可输入这三个字,在‘‘百度’’还是找不到,在‘‘搜狗’’也搜不着。除了圈内人,鲜有人知其名姓。
父亲生于老家的一个普通农家。父亲的父亲刘树金先生、母亲徐双兮女士一共生了12个孩子,哺育成长的仅有两男两女,父亲排行老三,上有兄姐,下有一妹。
父亲生前很少提及他的童年往事,许是不堪回首吧。从国家命运必然连着家庭兴衰的历史规律看,他应该吃了不少的苦。不然,深受爷爷怜爱的父亲,不会只上了三年学堂就开始做杂役。
新中国成立前夕,大概是1949年4月间,他被溃败的军抓过一次壮丁,还没走进兵营解放军就打过来了。他后来戏谑地说:‘‘错失了一次吃军饷的机会’’
父亲出道后,做过脚夫小贩,之后在鹰厦线(鹰潭-厦门)铁路建设工地打过三、四年工。1956年当了煤矿的矿工,一条命差点丢在井下。10年后举家下放回老家。1968年旋又只身招进钢铁厂,当了一辈子工人‘‘老大哥’’直至1980年退休。
从履历上看,父亲的一生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,平凡得如同一粒尘埃。可有时解读一个普通百姓,更有助于真实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那代人的人生价值取向,或许在一些日常琐事中也隐含着人生的哲思…
父亲很少讲故事,也不大善于讲故事,偶尔讲个故事,其目的性太明确、太直白。
小时候,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。大意是:从前有个富翁临终时,把一块写有勤俭两字的横匾交给两个儿子,并告诫他们:要想一辈子不受饥挨饿,就得照这两个字去做。
后来,兄弟俩分家时,将匾一锯两半,老大分得了一个勤字,分得一个俭字。老大很勤快,年年五谷丰登,但他老婆大手大脚,久而久之,家里就没有一点余粮。把俭字当作神谕供放中堂,却把勤字忘到九霄云外,每年所收粮食也就不多。有一年遇上大旱,老大、家中都早已空空如也。他俩就将勤俭二字踩碎在地。
这时候,突然有个路过的得道老人从窗外丢进一纸片,纸片上面写道:光勤不俭没积攒,光俭不勤等于零!兄弟俩恍然大悟,勤俭两字原来不能分家…
这故事虽然说教老套,可我一直记得。父亲更是以此作为信条,终身践行。
作为那个时代的工人父亲,他对勤俭两字的定位是:勤为邦,俭为家。父亲工作单位对他盖棺论定有这样一段话:‘‘他是勤劳的一生。常常最早一个上班,最晚一个下班,坚持出满勤、干满活,加班加点总有他的身影…’’是啊,父亲在哪都是这样拼命的干活。他在煤矿、钢铁厂工作期间,曾先后两次因工受重伤,皆因忘我工作所致。好几次被推荐为劳动模范,可最终没被授予,不过家里的茶缸、毛巾、脸盆等奖品,倒是不少。当然,他在家里是大家公认的‘‘劳动模范’’他起得早,自理生活能力强,洗衣、下厨房、搞卫生,手脚麻利,井井有条,很会生活。古稀之年还在路边垦荒种菜,一袋一袋地送到我们小家里。
父亲一度将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‘‘献’’改为‘‘显’’他如此解释:‘‘献’’字,有败财付出之意;而‘‘显’’字,则寓呈显祥瑞之兆。可见,他在‘‘俭’’方面是下足功夫的。
对父亲如此这般的省吃俭用,后辈们褒贬不一,毁誉参半。有的不以为然,觉得不够‘‘男人味’’还冠以‘‘铁公鸡’’名号。一段时间,我也不是很理解,曾多次劝说过,但收效甚微。
父亲历尽艰辛,一路跋涉,俭朴的品性如同他的勤奋一样,已成习惯。
当年他不到30元的工资,每月寄回20元,有时还有人情往来。难道他不想打一份红烧肉、来一瓶啤酒?难道他乐意一年四季都穿一身工作服?难道他喜欢过‘‘苦行僧’’的生活?不是的…临终前一段时间,他女儿60岁生日一出手便是罕见的厚厚红包,预备孙子、孙女结婚也是大大的红包。这是‘‘小气’’之人能做得出来的吗?
如此看来,人格的形式展示,并非一时可以窥探,有时看到的事实,却不一定真实!
父亲很男人的一面,体现在他的个性上。他一辈子率性刚直。
据说,父亲的性格承袭于爷爷。我出生时,爷爷已经过世好些年,他老人家到底怎样,只是一些传说,父亲的脾性却是亲历。不过,小时候,我们并没有受过父亲的呵斥、责打,或许是因为他没有与我们一起生活的缘故。从后来的经历看,父亲的确是个‘‘直肠子’’开口见心,不留情面。在他的人生字典里,很难找到‘‘委婉’’‘‘含蓄’’‘‘隐忍’’之类的字眼。
父亲的刚直,是明辨是非的刚直。父亲虽然脾气急燥,喜怒形于色,但他分得清是非曲直,对事不对人。他不喜欢小鸡肚肠、委委琐琐的人,不喜欢虚头八脑、吹吹嘘嘘的人,不喜欢游手好闲、讲究吃喝的人,不喜欢不讲仁义、寡廉鲜耻的人…这些人,他从不与之交往也不让我们靠近。若发现大家族中有此类人,经提醒仍无长进的,他一定不会有好脸色,有时还会寻机给其难堪。
父亲的刚直,是不记怨恨的刚直。我参军后,按政策村里每年应发给家里120元的义务兵优待金,可村里连续四年没兑现,父亲讨要无果便扬言要搬队里的水泵。没曾想,我一位本家堂叔背后给大队支招,说我家房子窄,不如叫人将水泵、水管一起搬进我家来。这位堂叔当年经济犯事还是父亲借钱让他过关的,现在以怨报恩,让父亲受不了,随即登门把堂叔骂了一通。当时堂叔脸红一阵白一阵,抬不起头来。不过骂归骂,兄弟还是兄弟,后来堂叔到家里,父亲一样热情招待,并不去揭疤说短。
父亲的刚直,是忍无可忍的刚直。他有一个姐姐—我的大姑母风烛残年时,当工人的老大和身边的,不尽孝道承担赡养义务,将全推给生活还不如他们的老幺,晚景凄苦。父亲最痛恨‘‘尽孝道不见人影,分财产镏铢必较’’的那种人,便几番上门找到论理,不但听不进,还对他出言不逊:‘‘你算什么…不关你事…管得太宽…’’父亲火冒三丈,劈头盖脸地将训斥一顿。接着他又找到当地村里要求处理解决,可村里的闪烁其词,并无主持公道之意。父亲咽不下这口气,第二天在老家请了四、五个年青力壮的汉子,再次前往兴师问罪。自知理亏,一看情况不妙就藏匿不出。但经父亲这一闹腾,此后大姑母的境况多少有些改观。
父亲的刚直,是亲疏有别的刚直。父亲并非‘‘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’’的侠客,见谁不顺就撸谁,他的火往往发在最亲近的人头上。我弟弟酷爱中国象棋,在地级市位居霸主地位,三天两头常与人对弈。父亲总觉得弟弟不务正业,一听说下棋就喋喋不休地数落,有时说的尖刻话,让我都下了台。我理解,父亲这样管着弟弟,一方面源于爱,一方面应该是证明他的存在和价值。我也尝过父亲不少的教训。有一回,我因工作繁忙,估摸有三个礼拜没有省亲,其间是否电话告知已忘记。父亲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,当时我楞了一下,说:‘‘您怎么来了?’’父亲淡淡而言:‘‘你没空来看我,还不允许让我看你吗?’’这话说得让我羞愧满面,无地自容…
照常理推测,像父亲这样个性很强、心直口快的人,应该不会有太多的至交朋友。然而,恰恰相反。父亲生前死后,有不少人惦记、怀念他。宜丰的老祝师傅、邻居老曾师傅多次给我打电话追思父亲。老曾师傅每每见到我,都为痛失父亲这样的好友而伤感落泪,老曾师傅说:‘‘比失去老伴还更难过…’’
如果有人认为父亲不懂爱,那是因为没走近他。不过,他的爱特别深沉,通常不会轻易表露。
在我10岁前,只知道父亲会在过年回家住上十天半月,一家人都把他当客待,对父爱的感受并不是那么深切。倒是父亲教我打算盘的烦闷、无趣的记忆,依稀残存。
第一次独自远足也是第一次走近父亲的生活,是我10时的盛夏某天。
那天,母亲火急火燎地从地里回家,一边擦着额头的汗珠,一边拉着我的手说:‘‘你敢一个人去爸那里吗?’’我说:‘‘敢!怎么了?’’母亲告诉我说,父亲受工伤住院了,因农忙走不开,让我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就这样,母亲把我送上火车,并请托一位大人途中照看我。
父亲住在集体宿舍平房,约有10余平米,同室4个工友,靠墙依次架有四张上下舖单人木床,下舖睡人,上铺放物品。晚上,我与父亲抵足而眠;白天,父亲有时安排我跟同室开汽车的一个老乡叔叔出车,有时让我同附近熟悉的几家小孩看连环画、玩耍,他自己不顾医嘱提前上班。吃饭由父亲从食堂打回宿舍,两个瓷碗各三两,菜直接扣在米饭上,父亲每次都有意将满的一碗递给我。
有一次,他将一份红烧肉让我一人吃了,自己推说伤后还不能吃荤。我在父亲那里呆了十天的样子,他送我上车回家,临别又一次紧紧抱着我,并叮嘱我:好好读书!
这次拥抱的十年后,我们父子又有一次相伴而眠的近距离接触。
那是1981年夏末,父亲让弟弟顶职上岗提前退休同母亲在老家,预备着我退伍回乡的营生。不知听了哪个战友老乡的传言,说我已考上军校了。于是,父亲兴冲冲地赶到部队来,准备帮我收拾行装送我上学。
这年我确实参加了军教导队的预提训练班考试,成绩也还好,可后来因名额什么的原因,不了了之。父亲从满心欢喜的峰巅,一下跌进无比失落的深渊。表面上看,父亲泰然自若,波澜不惊。白天趁我外出训练,还帮我洗军衣;晚上陪我聊天反倒安慰我。我陪他到西湖游玩,也强颜欢笑,不让我有丝毫觉察他失望的表情。
一周后分别,他拉着我的手说:‘‘我看你挺累的,你还是回家吧,我在家等你!’’那一刻,我竟无语凝噎…
回去后,父亲立马开山劈石,不到半年功夫,盖起一大间瓦房,等着我退伍归来…
母亲辞世后,父亲执意独自生活,孑然一身地看守空房,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,把家经营成母亲生前的那个模样,让子女有个温暖栖息之所。
过年过节早早地备好饭菜原料,盼着一家人团圆。儿孙辈喜欢吃的南瓜酱、红薯干,一样不拉地制作一大堆封装好。茶几上什么时候都摆着各样食品、水果,等着子女回家…
有一天晚上,我与父亲闲聊了很久,临别时他静静地说:‘‘有空多回来走走,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…记得爱惜身体,少抽烟,少喝酒,少熬夜…’’
我心一沉,表面上习惯性地诺诺应承着,出门偶然瞥了一眼墙上挂历,日子是农历十一月初四日,再看餐桌上两碟中午剩菜,顿时眼泪夺眶而出…那是父亲87岁生日!
写到这里,我的心情尤为沉重,父亲离世前几天在风中踽踽而行的身影,又浮现眼前…拈管怅思:这身影,是那个昂首离乡、独步天下的人么?是那个不畏艰难、双肩扛家的人么?是那个满腔血气、战天斗地的人么?是那个爱藏心间、恩泽子孙的人么?是那个…?
岁月风霜的利剑,一刀一刀地镌刻着父亲的容颜;生活暗河的激流,一浪一浪地冲击着父亲的身心,让这个身影从挺拔萎缩成佝偻。其实,这个身影,便是我明天的身影!解读父亲,就是解读自己。
斯人已矣,老去何殇?
面对‘‘父亲’’这个尊谓,我不由得反躬自省作为儿子的诸多缺失。
坦白地说,长此以往,我与父亲相处倾心交谈的话语并不多,高兴的事或不高兴的事常常缄口不言,父子间沉黙以对的场面多于欢颜笑语的场面;每每与父母通电话,习惯拨母亲的号码,拨不通时才会转向父亲,而且开头语往往是:‘‘妈妈去哪了?’’很少顾念父亲的心理感受;父母之间发生争吵,不是俩俩相劝,总是抱怨父亲这不该那不该,言语间颇多牴牾,说得父亲闷声一边;父亲吊影空寂时,自以为他身体尚好,常常今天出外奔波,明日好友应酬,不知有多少次让他倚门怅望;长大后,在我的记忆中,搜索不到陪父亲逛商场、看和送鲜花的画面,也没有对他说过‘‘我爱您’’的话。
现在说这些,已然于事无补,只会徒生愧疚、心绪不宁…
父亲是大山,是海洋,是背影…这些都是近、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常常描写父亲形象的主流词汇。于是,一代又一代的父亲便按照这样的版本,认认真真地塑造着父亲的形象。像大山,就得威严;像海洋,就得深沉;像背影,就得不露真容…
真是悲哀啊!我的父亲身上也有着无数中国父亲的缩影:满脸威气、不拘言笑、隐潜内心、独自担当…貌似的坚强,其实不堪一击,有时只需一句贴心的话语,就可以窥见其柔软的内心。我试图不做这样的父亲,然而不知不觉中,又变成了让人难以亲近、难以读懂的传统父亲形象的父亲。
高高在上的父亲,缺乏温度的父亲,不愿表达的父亲,让很多的父爱失落在时光的角落中而不被亲人触摸,这必然疏远父子(女)间的距离,成了子女敬而远之的亲人中最亲的陌生人。
我在日常交往中有时会问一些朋友:谁知道父亲的生日?谁能说清父亲的详细经历?谁能讲出一两个与父亲间的情感故事?回答大多让我失望,这恐怕是一个共性的社会问题。我说不清楚,这究竟是父亲的悲哀还是儿女的悲哀?
欣慰的是,倒是提到母亲,很多人都绘声绘色、滔滔不绝。母爱的伟大,使我们常常忽略了父爱的存在,不能不令人深思。
天下父母,子女懂得或不懂得、亲近或不亲近,爱就在那里,不增一分亦不减一分。父母根本不在乎子女怎样对待自己,他们都会始终如一地、掏心掏肺地、不求回报地默黙付出着,从不会为做给谁看而去爱。比如我的父亲。
为人父母自然希望自己洒下的心血和汗水,能滋养出一朵朵美艳的鲜花,即便滋养的是一棵小草也不觉得丢脸。只要延续自己生命的生命健康存在、快乐生活,让自己有机会与子女山一程水一程地同行一段,便可释然而去…
如果读不懂这一点,做子女的好像游离父母之心已经很远了。
有人说,送给父母的最好礼物是—荣耀;送给子女的最好礼物是—榜样。后者我赞同,前者不敢苟同。那么,年节或是生辰,表达对父母的爱意和感恩,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?一个拥抱?一束鲜花?一份?都不是。离得远,一个电话足矣;靠得近,最好回家。儿孙绕膝承欢时,那是父母最幸福的时刻......
但愿我的解读,能让父亲含笑九泉…
长相思•冬祭
风飕飕。雨飕飕。梧叶飘萧何日休。潮思涨满楼。
眉也愁。心也愁。不到来生不到头。赣江和泪流。
2017年5月18日完稿
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:
父亲
父亲,读音:“fùqīn”,口语叫“爸爸”,一个人直系血统的上一代男性。父亲,一词书面语色彩较浓,一般不作为面称。
男孩
《男孩》是梁博演唱的歌曲,由梁博创作词曲并编曲,并由梁博在湖南卫视《歌手2017》首演。
- 上一篇:天才黄金手 第十五章 定计
- 下一篇:巫师之旅 第七百六十九章 困迹封印(完)